至于这批货款,怡和洋行已经支付了庄票,用视为完成了付款义务,后来生钱庄倒闭的意外,不用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双方各执一词,但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能撤诉,怡和愿意另以真金实银支付货款。如此一来,怡和在此单生意中损失8万两银子,北华捷报认为这还是合算的,毕竟怡和因此薄了在中国的声誉。
这件案子以怡和洋行权衡利弊,以损失挽回名誉结束,但是影响非常坏,直接冲击到了华商的世界观。
华商觉得,连怡和这样的“东方罗斯柴尔德”也会在需要的时候,拒绝承认那些实际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的身份,这是个危险的行为,这让他们对洋 充满了不信任,他们认为有必要堵租个漏
充满了不信任,他们认为有必要堵租个漏 。
。
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先行动起来。
行会出台了新的行会规则,并且提 给了上海道台,并知会外商商会。
给了上海道台,并知会外商商会。
丝绸行会规定所有 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通译翻译,其实就是买办),否则不得进行。这一规定,让那些未经过在中国行会注册的买办及其背后的洋行,失去了直接向中国商行采购的权利。
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通译翻译,其实就是买办),否则不得进行。这一规定,让那些未经过在中国行会注册的买办及其背后的洋行,失去了直接向中国商行采购的权利。
同时在结算方面,行会提出,虽然华商们都希望进行现款 易,但毕竟数额巨大,而且丝绸的品质鉴定相当复杂,现款
易,但毕竟数额巨大,而且丝绸的品质鉴定相当复杂,现款 易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行会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只要货款未能全额付清,该批丝绸即使已经装船,也不得视为外商的财产。一旦生意外,比如期间洋行倒闭,承兑的钱庄或银行
易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行会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只要货款未能全额付清,该批丝绸即使已经装船,也不得视为外商的财产。一旦生意外,比如期间洋行倒闭,承兑的钱庄或银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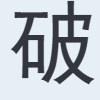 产,则华商可以蓉该批货物。此前,只要货到了外商手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
产,则华商可以蓉该批货物。此前,只要货到了外商手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
上海丝绸行会的这种规定,显然对华商的风险进行了规避,因此洋 极其不满。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在上海
极其不满。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在上海 岸的中国商
岸的中国商 非常团结,谁敢不经过行会而跟洋
非常团结,谁敢不经过行会而跟洋 私自做生意,都会受到全体商
私自做生意,都会受到全体商 的抵制。结果洋商最后只能屈服,毕竟这个时代,还是中国商
的抵制。结果洋商最后只能屈服,毕竟这个时代,还是中国商 的买方市场。英商不跟这些行会合作,法商会合作,比利时商
的买方市场。英商不跟这些行会合作,法商会合作,比利时商 会合作≤之他们遇到了十三行时代的窘境,那就是蜂拥而至的洋商,无法跟用各种中国式关系拧成一
会合作≤之他们遇到了十三行时代的窘境,那就是蜂拥而至的洋商,无法跟用各种中国式关系拧成一 绳的中国商
绳的中国商 集团对抗。
集团对抗。
商业竞争,说白了还是一个财力的竞争,零散的西方散商在这个时代确实还无法跟垄断经营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商 集团竞争,但是时代在改变。
集团竞争,但是时代在改变。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让从伦敦到上海12o天的船期,缩短到了55天到6o天,洋 突然不需要提前储备半年的货物了,他们进货变得从容了,他们不需要跟财力雄厚的大行会直接提货,而可以慢条斯理的使用他们培养出来的买办
突然不需要提前储备半年的货物了,他们进货变得从容了,他们不需要跟财力雄厚的大行会直接提货,而可以慢条斯理的使用他们培养出来的买办
 内地进货了。电报的开通,也让他们能够紧跟欧洲的市承
内地进货了。电报的开通,也让他们能够紧跟欧洲的市承 ,极大的规避进货的风险,技术的进步,让他们的力量变得强大了。华商是有本地优势,但是他们掌握的是世界市场的优势。
,极大的规避进货的风险,技术的进步,让他们的力量变得强大了。华商是有本地优势,但是他们掌握的是世界市场的优势。
此消彼长之下,洋 觉得自己实量了,越不愿意接受中国商
觉得自己实量了,越不愿意接受中国商 组织的不平等规定。
组织的不平等规定。
洋 的第一次反击是在茶叶贸易领域,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规定只准蒸汽
的第一次反击是在茶叶贸易领域,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规定只准蒸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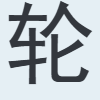 船通行。大量的蒸汽
船通行。大量的蒸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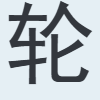 船迅地取代飞剪船,投
船迅地取代飞剪船,投 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
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 额中占了7o-8o%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缩短一半之后,运费和保费变得更为低廉。中国茶叶经由蒸汽
额中占了7o-8o%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缩短一半之后,运费和保费变得更为低廉。中国茶叶经由蒸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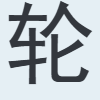 的快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逞不再需要维持六至十二个月的茶叶库存。
的快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逞不再需要维持六至十二个月的茶叶库存。
加上大明大规末大了茶叶生产能力,导致生产本就已经饱和,于是在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开始下跌,而上海的华商商会依然试图控制茶价,这一次洋 不接受了,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红,洋
不接受了,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红,洋 一时间也拒绝进
一时间也拒绝进 。这一次洋
。这一次洋 胜利了,最后他们给上海茶叶的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
胜利了,最后他们给上海茶叶的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
在洋 慢慢在茶叶领域占得先机的时候,在丝绸领域,华商组织依然垄断着贸易价格。
慢慢在茶叶领域占得先机的时候,在丝绸领域,华商组织依然垄断着贸易价格。
因为这几年的丝绸行业,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从普法战争开始,世界丝绸价格翻着翻上跳,尽管广東飞展的机器织稠业赶上了东风,但是对上海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广東丝绸主要是中低端,而上海的丝绸则走的是高端。
江南苏湖一带出产的上等白丝,手工作坊织就的丝绸,依然大量出 西方市场。但是连续两年这种上等丝绸都以7%到8%的度增长,让商
西方市场。但是连续两年这种上等丝绸都以7%到8%的度增长,让商 们大量出
们大量出 这种货物。航运大提后,丝绸
这种货物。航运大提后,丝绸 易度和频率加快,丝绸出
易度和频率加快,丝绸出 在当季的
在当季的 2-3个月就完成了。
2-3个月就完成了。
各种利好刺激的上海市场过了负荷能力。丝绸的质量问题,在急增的出 需求拉动下
需求拉动下 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1872年5月,里昂丝绸商会向上海西商公所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赶出法国市场。
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1872年5月,里昂丝绸商会向上海西商公所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赶出法国市场。
此时已经在普法战争后的混 中走出来的法国,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推动下,他们开始快恢复他们的丝绸生产能力,国际丝绸价格大幅度下降,洋商开始在上
中走出来的法国,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推动下,他们开始快恢复他们的丝绸生产能力,国际丝绸价格大幅度下降,洋商开始在上